-
-
五猖会的开篇便为参加赛会营造出浓厚的氛围,先是回忆起童年观看赛会的情景,再引述《陶庵梦忆》中热闹非凡的赛会场面,接着描述自己亲眼见过的较为隆重的赛会,这一切都为描绘五猖会做了充分铺垫。然而,笔锋一转,写到父亲要求“我”背书,这让“我”极度失望和郁闷,最终虽然背书成功,得以去看五猖会,但心情已大不如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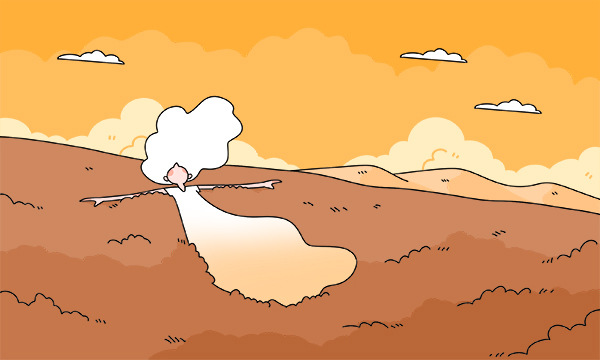
孩子们除了过年过节,最期盼的恐怕就是迎神赛会了。但我家地处偏僻,赛会行列经过时已是下午,仪仗等也大为缩减,所剩寥寥无几。常常伸长脖子等候多时,却只见十几个人抬着一个神像匆匆跑过,于是,赛会便结束了。
我常常怀有一个希望:希望这一次的赛会比前一次更加繁盛。然而结果总是“差不多”,留下的唯一纪念品便是在神像抬过之前,花一文钱买下的用烂泥、颜色纸、竹签和两三枝鸡毛做成的哨子,吹起来发出刺耳的声音,叫作“吹都都”,吡吡地吹上两三天。
如今读《陶庵梦忆》,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华奢侈至极,尽管明人的文章或许有些夸大。为祷雨而迎龙王,现在仍有此习俗,但办法已大为简化,不过是十多人盘旋着一条龙,再加上村童们扮些海鬼。那时却还要扮演各种故事,而且实在精彩绝伦。他记述扮演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时说:“……于是分头四处寻找,找黑矮汉,找梢长大汉,找头陀,找胖大和尚,找茁壮妇人,找姣长妇人,找青面,找歪头,找赤须,找美髯,找黑大汉,找赤脸长须。在城中大肆搜寻;如果没有,就到城郭、乡村、山僻之处,甚至邻府州县去寻找。用重金聘请,得到三十六人,梁山泊好汉,个个栩栩如生,整齐有序,人马协调前行……”这样的白描活现的古人,谁能不心生一看的雅兴呢?可惜这种盛举,早已和明朝一同消逝了。
赛会虽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、北京的谈国事那样为当局所禁止,但妇孺是不许看的,读书人即所谓士子,也大多不肯前去观看。只有游手好闲的闲人,才会跑到庙前或衙门前去看热闹。我关于赛会的知识,多半是从他们的叙述中得来的,并非考据家所看重的“眼学”。然而我记得有一回,也亲眼见过一场较为盛大的赛会。开首是一个孩子骑马先来,称为“塘报”;过了许久,“高照”到了,长竹竿挑起一条很长的旗,一个汗流浃背的胖大汉用两手托着;他高兴的时候,就肯将竿头放在头顶或牙齿上,甚至鼻尖。接下来是所谓的“高跷”、“抬阁”、“马头”等;还有扮犯人的,红衣枷锁,其中也有孩子。我那时觉得这些都是极为光荣的事业,能参与其中便是大有运气的人——大概是因为羡慕他们的出风头吧。我想,我为什么不生一场重病,让我的母亲也到庙里去许下一个“扮犯人”的心愿呢?……然而直到现在,我终于没有与赛会发生过任何关系。
即将去东关看五猖会了。这是我儿时所罕遇的一件盛事,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大的会,而东关又离我家很远,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,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。一是梅姑庙,就是《聊斋志异》所记载的,室女守节,死后成神,却篡夺了别人的丈夫;现在神座上确实塑着一对少年男女,眉开眼笑,颇与“礼教”相悖。另一座便是五猖庙了,名目就颇为奇特。据有考据癖的人说:这就是五通神。然而也并无确凿证据。神像是五个男人,也不见有什么猖獗的样子;后面列坐着五位太太,却并不“分坐”,远不及北京戏园里界限之严格。其实呢,这也是与“礼教”相悖的——但他们既然是五猖,便也无法可想,而且自然也就“另当别论”了。
因为东关离城远,所以大清早大家就起来了。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,已经停泊在河埠头,船椅、饭菜、茶炊、点心盒子,都在陆续搬上船去。我笑着跳着,催他们快点搬。忽然,工人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,我知道有些不对劲,四面一看,父亲就站在我身后。
“去拿你的书来。”他缓缓地说。
这所谓的“书”,是指我开蒙时所读的《鉴略》。因为我没有第二本了。我们那里上学的年龄多选单数,所以我记得我那时是七岁。
我忐忑不安地拿了书来。他让我和他一起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,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。我担着心,一句一句地读着。
两句一行,大约读了二三十行,他说:
“给我读熟。背不出来,就不准去看会。”
他说完,便站起来,走进房里去了。
我仿佛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。但是,有什么办法呢?只能是读着,读着,强记着——而且要背出来。
粤自盘古,生于太荒,
首出御世,肇开混茫。
就是这样的书,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,别的都忘记了;那时强记的二三十行,自然也一同忘却了。记得那时听人说,读《鉴略》比读《千字文》、《百家姓》有用得多,因为可以了解从古到今的大概,那当然是很好的,然而我一字也不懂。“粤自盘古”就是“粤自盘古”,读下去,记住它,“粤自盘古”呵!“生于太荒”呵!……
需要的东西已经搬完,家中由忙乱转为寂静。朝阳照着西墙,天气很晴朗。母亲、工人、长妈妈即阿长,都无法救我,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,而且背出来。在寂静中,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,将什么“生于太荒”之类的句子夹住;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,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。
他们都在等候着;太阳也升得更高了。
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,便站了起来,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,一口气背了下去,梦似的就背完了。
“不错。去吧。”父亲点着头说。
大家同时活动起来,脸上都露出了笑容,向河埠走去。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,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,快步走在最前头。
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。开船以后,水路中的风景、盒子里的点心,以及到了东关五猖会的热闹场面,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。
直到现在,别的都完全忘记了,不留一点痕迹了,只有背诵《鉴略》这一段经历,却还如同昨日之事一般分明。
我至今一想起,还诧异我的父亲为何要在那时叫我来背书。
五月二十五日。